

成效追蹤
08
2017-06
蔣文龍——深耕“三農(nóng)” 麥秀兩岐
作者 ? admin
編者按:近日,中央新聞單位駐浙記者聯(lián)合會在杭州舉辦研討會,專題研討蔣文龍的“三農(nóng)”報道。作為農(nóng)民日報駐浙江記者站站長,多年來,蔣文龍圍繞浙江農(nóng)業(yè)、農(nóng)村的改革發(fā)展和農(nóng)民的生存狀態(tài)、利益關(guān)切,深入基層,深耕“三農(nóng)”,麥秀兩岐,采寫了大量報道,受到廣泛關(guān)注。他的作品與成果,也獲得與會領(lǐng)導(dǎo)、專家的充分肯定。這里,選登兩位專家的評點,以饗讀者,并供業(yè)界同仁品鑒。
研究型記者的四種能力和四個維度
浙江大學(xué)新聞系主任 沈愛國
蔣文龍是一個專家型記者,這幾乎已經(jīng)是一個共識。我本來打算說一個題目,叫“蔣文龍——專家與文人的合體”。因為在他身上,有非常顯著的學(xué)者氣質(zhì)和文人風(fēng)范:說話慢吞吞,文縐縐,待人溫和,肚里有貨,很有涵養(yǎng)。
但是,為了避免重復(fù),更主要是為了顯得與眾不同,我最后還是選擇了一個“研究型記者”的概念。發(fā)言的題目就叫:《研究型記者的四種能力和四個維度》。
第一種能力是感知力。
一個研究型記者,首先必須是一個出色的新聞人。所謂感知力,就是敏銳的觀察能力,捕捉新生事物的能力,超人一等的新聞敏感。感知力,來源于生活,來源于日常的積累和訓(xùn)練,表現(xiàn)為思維火花的閃現(xiàn),電光火石之間,眼睛一亮,思維豁然開朗。
在蔣文龍的作品集——《麥秀兩岐》一書中,好多作品都體現(xiàn)了高超的新聞敏感。有些報道的標(biāo)題就非常吸引人,新聞性特強,新聞價值高。
比如《浙江旱糧成“新寵”》一文,說的是番薯和土豆這類當(dāng)年上不了臺面的農(nóng)產(chǎn)品,搖身一變成了消費者眼中的“寵兒”,反映的是消費者的多元需求,以及政府引導(dǎo)有方,推動有力。
《杭州:智慧農(nóng)業(yè)正當(dāng)時》這篇報道,抓住的新聞點是:杭州的智慧農(nóng)業(yè)集成了物聯(lián)網(wǎng)、云計算等信息技術(shù),只要輕點鼠標(biāo)或者操作手機,就可以提供精準(zhǔn)化種植、可視化管理、智能化決策,大步邁入了農(nóng)業(yè)發(fā)展的高級階段。“電子保姆”管理石斛,手機種葡萄,聽聽名詞都讓人神往。
再比如《飯店門前擺粥攤》《一顆櫻桃的72小時旅行》等新聞篇目,都是新聞價值高、讓人耳目一新的出色報道。
第二種能力是思辨力。
思辨能力,就是記者對新聞事實進行由表及里的分析,由淺入深的比較,從而對新聞事物進行多層次、多方位、多角度的立體式反映。由點及面,由現(xiàn)象到本質(zhì),在作品中寓理于事,以事明理?;蛘哒f,也就是根據(jù)報道主題需要,抓住事物特點,通過對具體事實的描述和敘述,深入分析,總結(jié)規(guī)律,上升到一定的理論層面,增加新聞報道的思想性和厚重感。
《麥秀兩岐》中有以下篇目,都是思辨力的產(chǎn)物。
比如《“互聯(lián)網(wǎng)+農(nóng)業(yè)”如何加——對浙江遂昌、臨安兩地的分析》,探討中國最為年輕的互聯(lián)網(wǎng)如何與最為傳統(tǒng)的農(nóng)業(yè)產(chǎn)業(yè)相加。一系列的調(diào)查研究之后,發(fā)現(xiàn)縣域經(jīng)濟電商化正在席卷中國農(nóng)村,而品牌化在其中有獨特的作用。
再如《豬是怎么飛起來的——浙江龍珠畜牧專業(yè)合作社的養(yǎng)豬經(jīng)》,蔣文龍用他最擅長的提問式標(biāo)題,把問題擺在讀者面前,最后用他深入的分析和思考、嚴(yán)密的邏輯,把答案呈現(xiàn)出來,讓人受到啟發(fā),得到借鑒。尤其是這篇通訊的開頭寫得非常吸引人:
“艾格非”養(yǎng)豬,很快偃旗息鼓;“高盛”養(yǎng)豬,至今生死未卜;“網(wǎng)易”養(yǎng)豬,人們形容是“紙上談兵”。養(yǎng)豬血本無歸的案例如今比比皆是,驚心動魄。
然而,浙江龍游的一家本土合作社,短短四年時間,用連橫合縱之法,將農(nóng)業(yè)產(chǎn)業(yè)中最傳統(tǒng)的生豬養(yǎng)殖,做得風(fēng)生水起。人們形容,“龍珠”的豬會“飛”。
還有《破題“股份制農(nóng)場”——浙江仙居縣農(nóng)村改革的創(chuàng)造性跨越》,以及他的另一作品集《龍行浙江》中的《不包辦不圖利不冒進——鄞州農(nóng)房改造中的哲學(xué)思辨》,這兩篇工作通訊,通篇讀下來,理性思考多,思辨色彩濃,體現(xiàn)了作者的思想深度。
蔣文龍在《龍行浙江》的后記中說:進農(nóng)民日報后的第一篇報道是義烏農(nóng)貿(mào)城,他不愿意寫成泛泛之作,要求自己總結(jié)提煉它的成長發(fā)展規(guī)律,對其他地方能夠有所借鑒。從此,深度報道就成了追求和特色,大量查閱資料,不斷琢磨,不斷打磨。對每一個新聞素材,都習(xí)慣于放到整個“三農(nóng)”發(fā)展的大背景下進行審視,不斷提出“為什么”“怎么辦”,去思考現(xiàn)象背后的本質(zhì),分析問題產(chǎn)生的原因,總結(jié)事物發(fā)展的規(guī)律。
第三種能力是預(yù)見力。
預(yù)見能力,也可以叫做前瞻能力,指的是研究型記者,善于以當(dāng)下社會形勢或者客觀事物的現(xiàn)狀為基礎(chǔ),為依托,對未來的發(fā)展前景和趨勢,進行預(yù)測和展望。
蔣文龍就是這樣的研究型記者。他站在歷史的制高點和時代的最前沿,總攬全局,并通過深入的調(diào)查研究,從已知推及未知,洞察趨勢和未來。他能夠認(rèn)識到重大事件背后的深層意義,預(yù)見到未來發(fā)展中將提倡什么,反對什么,主動掌握發(fā)稿時機,取得更大更好的傳播效果。
我在這里簡單羅列一下這一類報道的篇目,比如《麥秀兩岐》中的《農(nóng)業(yè)電商,阿里造夢》,《龍行浙江》中的《產(chǎn)業(yè)化組織形式的浙江創(chuàng)新——可望破解產(chǎn)業(yè)化帶來的一系列問題》。具體報道內(nèi)容,我就不再重復(fù)。
第四種能力是創(chuàng)新力。
創(chuàng)新能力,就是指研究型記者永不滿足,積極進取,勇于開拓,不唯書、不唯上,不為現(xiàn)成的各種新聞發(fā)布會材料所束縛,不為現(xiàn)有的各種結(jié)論所左右,獨立思考,敢于觸碰熱點和難點,敢于發(fā)出獨特的聲音,提出獨到的見解。
正如胡宏偉的《溫州炒房團》提出的觀點:
今天,我們所知道的“炒房團風(fēng)潮”,是一個天大的、被操縱著的謊言, 迄今最詳盡的溫州炒房團真相,誰是溫州炒房大戲的主角,他們的炒房資本到底有多少?炒房團是否“有組織有預(yù)謀”,“炒房路線圖”從何而來?究竟是什么人導(dǎo)演了這場合謀的財富游戲?“溫州炒房秀”透射出了中國社會經(jīng)濟哪些危隊的脈象?
書評:溫州炒房團的故事已經(jīng)過去很久了。但在社會上,事情的真相卻未必被很多人所知道。作者的最大貢獻,就是履行了一個新聞記者的最基本職責(zé),客觀地揭示了真相。在經(jīng)濟權(quán)力漸趨主導(dǎo)之下的社會,這需要良知和勇氣。
蔣文龍的《龍行浙江》一書中,也有好多這樣的篇目,追求特立獨行,抵制隨波逐流,努力發(fā)出自己的最強音,提出有創(chuàng)造力的觀點,振聾發(fā)聵,讓人警醒。比如《農(nóng)業(yè)會展:盛宴過后須深思》《胡柚悲歌》等等。
作為一位出色的研究型記者,蔣文龍身上的優(yōu)秀素質(zhì),還可以從他所采寫的報道的四個維度來解讀。他的許多長篇通訊,具備了足夠的傳播力、影響力、引導(dǎo)力和公信力;他所做的每一次探索和嘗試,都體現(xiàn)了“多人一點,快人一步”的新聞競爭理念。
四個維度具體闡述如下:
第一是高度。所謂報道的高度,就在于是否能夠準(zhǔn)確地把握時代脈搏。比如像改革開放30年、新中國成立60周年、建黨90周年等等,對中國發(fā)展而言,無疑是具有重要歷史意義的時間節(jié)點;像轉(zhuǎn)變經(jīng)濟發(fā)展方式、加強社會管理創(chuàng)新、黨員先進性教育、干部隊伍作風(fēng)建設(shè)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(shè)等等,也是某個發(fā)展階段的戰(zhàn)略主線。只有深刻領(lǐng)會這些重大主題的戰(zhàn)略意義,用新聞專業(yè)視角進行思考,這些報道才有靈魂,才有高度。蔣老師采寫的許多報道,在題材上往往具有重大性、時代性和前瞻性的特點,充分發(fā)揮了“輿論引導(dǎo)先行軍、政府決策參謀者、先進理念傳播器”的作用。
二是廣度。這個廣度包含三層意思。一是指報道題材范圍廣。《龍行浙江》的目錄中,設(shè)置的欄目名稱,可見一斑:“本報浙江特別報道”“新聞深一度”“直擊杭州三農(nóng)”“縣域發(fā)展多棱鏡”“人物面對面”“觀察與比較”“城鎮(zhèn)解剖”“營銷解密”“微觀主體新觀察”“獨立思考”等等。二是指作者的思維開闊,思想靈動,縱橫捭闔,汪洋恣肆。三是傳播范圍廣,報道影響面大,社會關(guān)注度高。
三是深度。蔣文龍報道的深度,也可以區(qū)分為兩個不同的層次。
首先是獨特性,就是“人無我有,人有我優(yōu)”,所謂“見人之所未見,言人之所未言”,看到了別人看不到的東西,說出了別人說不出來的話,這是一種深度。
其次是深刻性,就是報道能夠觸及到常人一時難以認(rèn)識、一時難以把握的事物的本質(zhì),揭示了問題的核心和思想的精髓。這樣的報道,那就必然是有深度的。
深度在于準(zhǔn)確地挖掘思想內(nèi)涵。沒有思想性,再精美的文字也打動不了讀者。蔣文龍的許多報道,常常為地方黨委和政府科學(xué)決策,提供大量一手資料和思考建議。這也是深度的體現(xiàn)。
四是溫度。這主要是指蔣文龍身上的文人氣質(zhì)和人文情懷。
比如作品集取名為《麥秀兩岐》,說的是一株麥子長出了兩個穗子。屬于豐收之兆,多用來稱頌吏治成績卓著。這個成語典故出自《藝文類聚》。不是中文系畢業(yè)的,恐怕大都不知道。
溫度的第二層意思,就是報道中要包含人情味、故事性,報道中要時刻體現(xiàn)出人文關(guān)懷。最近說得多的幾句話,可以拿來作為參考:“宣傳新聞化,新聞故事化,故事細(xì)節(jié)化,細(xì)節(jié)生活化。”報道的生活味和人情味,可以提高新聞的傳播力,增強新聞的感染力。
蔣文龍一次次的采訪調(diào)研,基本上都是做到了“腳到、眼到、耳到、心到”。他的采訪作風(fēng)很扎實。報道的語言風(fēng)格,也有許多清新靈動的閃光之處,努力增加新聞的可讀性。但總體上來說,因為非事件性新聞數(shù)量偏多,工作性通訊偏多,思辨性的內(nèi)容較多,有時顯得專業(yè)性太強、通俗性不夠。今后在文本寫作上,似還可以增加更多的故事、情節(jié)和細(xì)節(jié)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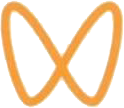




 下一篇
下一篇